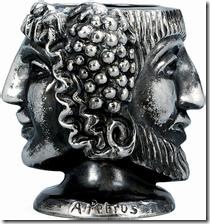秋风飒起,路边鸣蛙终于停止了悲戚惨淡的歌声,树上的鸣蝉总算完成了扰乱夏日安详气氛的使命,惟有耳边秋风不绝吹息,带来些许阴冷气息。云很黯淡,天色很黯淡,感受不到阳光所带来的一丝快慰——今天的阳光也很黯淡。路边几棵枯残的梧桐可怜地摇晃着黄叶,以示生命的存在,可这好不自然呵,叶子抖出的,只有凄凉的气息。
秋风飒起,路边鸣蛙终于停止了悲戚惨淡的歌声,树上的鸣蝉总算完成了扰乱夏日安详气氛的使命,惟有耳边秋风不绝吹息,带来些许阴冷气息。云很黯淡,天色很黯淡,感受不到阳光所带来的一丝快慰——今天的阳光也很黯淡。路边几棵枯残的梧桐可怜地摇晃着黄叶,以示生命的存在,可这好不自然呵,叶子抖出的,只有凄凉的气息。
忽然,我停下脚步,耳边的风似乎也停止了呼吸,凝结、冻僵。不远处一个穿着半敞西装的中年男子,半躺在马路上,须发缠结,蓬头垢面,原本似乎体面的一套西服布满了裂口皱褶和油迹泥印。
又一个新千年 “金秋” 的乞丐。
我开始走近他,很不自然的脚步。他淡漠的眼神忽然露出生气,一个哀怜万分的表情,十足的可怜虫。我微
[……]阅读全文